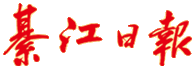

版次:04 来源: 2024年05月15日

北宋熙宁四年(1071年)建造的摩崖瘗龛。

文化服务志愿者辨识北宋熙宁五年(1072年)古代摩崖碑刻。
古代,皇帝被尊为真龙天子,再高贵的王公大臣,也只能着爪上只有四趾的蟒袍。因此,民间传说,都喜欢把沾龙的地名,与皇帝的活动关联起来,龙登山亦不例外。虽然,前几期“綦走发现”,已经否定了其因宋太祖赵匡胤、明太祖朱元璋、建文帝朱允炆、大夏太祖明玉珍登临而名的说法,但是,龙登山真的与皇帝没有关系吗?那倒未必。
大晟南吕编钟,宋廷御赐?
民国《江津县志》卷十五《金石》载,“龙登山寺有铜佛三,高约八尺,相传明成化间(1465-1487年)铸造。”接着提行介绍,“宋太祖初,于宋地掘得周宋公成(东周春秋时期宋国君主,名成)铸经钟六,以为受命之符,因作《大晟乐》。仍其制,铸编钟十二,其一藏邑人戴登俊家。高周尺(周代的尺度)一尺,围一尺八寸,两旁鼓间左右刻“大晟”“南宫(‘宫’疑为‘吕’之误)”各二字。”
不过经南宋赵九成《续考古图》《宋史·徽宗本纪》等史志记载,北宋的大晟编钟,却是铸成于赵匡胤驾崩129年后的宋徽宗崇宁四年(1105年)。铸12套,每套正声、中声各12枚,清声4枚,共336枚,以再现先秦雅乐。
二十二年后的“靖康之耻”,这336枚大晟编钟或被掳走,或埋入地下,或随宋廷南迁,因此散失流落,目前仅存30余枚,故宫博物院的大和(避金太宗完颜晟讳,而抹去“大晟”,新刻“大和”)夹钟、辽宁省博物馆的大晟南吕、开封市博物馆的大晟夷则,都是难得的国宝。
该志《金石》部分其它条目,都是地点+宝藏+规格等描述。同一大地名又套多个小地名各有藏宝的,是紧随大晟编钟后的“县属崇兴场(龙登寺北约10公里)川主庙明代铁钟……朝阳寺明代云板……又附近玉皇观铁灯杆……”但并没有提行分述。唯有大晟编钟例外,是叙事+宝藏+收藏人+规格等,没有收藏人具体住家小地名,其前地址只有龙登山寺。但在龙登山附近的津、綦一带,戴姓属于旺族,西约10公里亦有一戴家祠堂。又因古人书写习惯,文中如果涉及皇帝名号或圣、旨等特殊字词,即使该句并没有结束,一般会提行另书。崇兴场后一条,地点是“黄泥场附近金紫沟古庙颓垣中钟一……”亦在龙登山西不远处。据上综合判断,大晟编钟收藏人住在龙登山附近的可能性最大。
龙登山附近能拥有其中一枚宋廷乐府重器,可能也是宋廷南迁后的御赐。只是不知道,是否还留存于世。也许,这可能也是明万历《四川总志》起,有关江津的方志,开始附会“宋太祖潜时常登龙登山”的依据之一。
敕赐禅居古寺,源自唐代
南宋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八十《南平军》载,“龙登山……上有禅居寺,在唐为灵岩寺。”把龙登山的历史,提前到了距今至少1017年的大唐时代。
但文化服务志愿者们遍查明清时期的《四川总志》《四川通志》及《江津县志》,龙登山上仅有龙登寺、千佛岩两处寺观记载,并无禅居寺、灵岩寺。
清乾隆《江津县志》卷之二《古迹》载,“巨蠏泉(详见上期‘綦走发现’‘祈雨巨蟹古泉,大旱薄收’部分),一在石佛寺后,一在禅居寺前。”没有明确禅居寺的位置。民国《江津县志》卷一《名胜》中又明确“巨蠏泉,在骆騋山禅居寺。”龙登山与骆騋山,相距约二十公里,都属于江津东南方向名山,想来不会记错。难道是《舆地纪胜》有误?
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牛英彬在《2021年重庆石窟寺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》中介绍,“江津龙登山发现较多唐宋时期摩崖瘗(yì)龛、摩崖瘗塔,这类遗存在川渝地区石窟寺中较为少见,对研究僧人瘗埋制度及石窟寺的功能分区有重要价值。”通过考古发掘把龙登山的历史明确到唐宋时期。
在2024年3月10日的实地发掘中,文化服务志愿者们自然不会放过专业考证的重磅遗存。“綦走发现”团队是“大众考古”,仅从形制看不出门道。幸好在多块摩崖题刻中辨认出“熙宁四年(1071年)”“熙宁五年”“隆兴二年(1164年)”“乾道元年(1165年)”“乾道九祀(1173年)”“淳熙元年(1174年)”,以及“乾道九祀”之前的“庚子年(1120年,即北宋徽宗宣和二年)”共七个宋代年号,可窥龙登山在两宋时期佛寺香火之旺盛。
其中一块摩崖题刻碑在一窟摩崖佛龛下方,离地约1.5米高的石壁上,高54厘米、宽45厘米,是约100字的《释迦弥》。其中从“僧从政,昔者发心伏为出家,和尚前生父母,四恩三友,自捨■仟钱镌造释迦佛、阿难迦叶一龛,永为供养,祈乞法躰延远,寿算遐长,永镇千春,四躰宁律”数句,可知从政和尚出生佛教徒家庭,其俗家父母还在此施有功德留下石窟佛像。用心敬瞻,不同妆容、不同姿态、不同器仗,有站有坐、有仰头有躬身、有大笑有深忧、有安详有无措……仔细数来,共刻有108座,其中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佛像各36、31、31座,十缠众生像10座。将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王恩、三宝恩,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(义同三界,即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)的佛教“四恩三有(友,通‘有’)”,佛与人相生相伴,和谐共处,一切众生平等理念在方寸之间展现出来。
“勅(chì,同‘敕’)赐禅居寺僧从政……时以熙宁五年六月十五日,勅赐禅居寺僧从政亡过。”《释迦弥》首尾两句,不但证实了《舆地纪胜》记载禅居寺在龙登山的真实性和民国《江津县志》将“禅居寺”定位在骆騋山的失误,还表明了曾受到皇家敕赐的高贵身份。至于是唐皇还是宋帝的敕封,还需继续考证。据了解,包括綦江在内的渝南黔北地区,另外只有扶欢镇崇恩寺,最迟在北宋元祐八年(1093年)享受过皇恩赏赐。
禅居寺僧从政,谁受敕赐?
在古代,出家为僧需要官方许可证——度牒,而宋代取得度牒只有三种途径:一是试经,规定念经(背诵)百纸或读经五百纸合格,保障僧侣佛学质量。二是恩度,即朝廷恩准和德行考量的免试,但只针对有敕额寺院的童行(是指发心求道,进入寺院为沙门而尚未剃度之幼童、少年,前者称童子,后者称行者,合称童行),数量极少。如北宋诗人赵鼎臣《竹隐畸士集》载,赵州(今河北赵县)大禹寺“今来欲乞朝廷详酌,依崇宁二年(1103年)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挥,特赐本寺一敕额,岁许度僧一人。”三是进纳,北宋中叶开始,童行欲披剃者可以用钱购买度牒。有观点认为,摩崖碑刻《释迦弥》中的从政和尚可能属于第二种情况,即该碑文中“敕赐”对象是从政和尚。
对此,文化服务志愿者们看法不同,认为受到“敕赐”的是禅居寺。一是“恩度”是出家的一种方式,“敕赐”是皇帝的赏赐,意思完全不同。如果从政和尚仅是恩度出家,是不能冠以“敕赐”的。二是如果“敕赐”的是从政和尚,碑刻原句顺序应为“禅居寺敕赐僧从政”,而不是现在的“敕赐禅居寺僧从政”。
既然龙登山禅居寺在北宋就曾受到皇帝的赏赐,宋廷南迁后,大量官员、文人随之深入西南腹地,禅居寺又能得到朝廷更多关注,是符合人情世故的,所以《舆地纪胜》会给予记载,前面介绍的大晟南吕编钟,是在南宋流入龙登山的可能性再次增大。
(未完待续)
文图/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